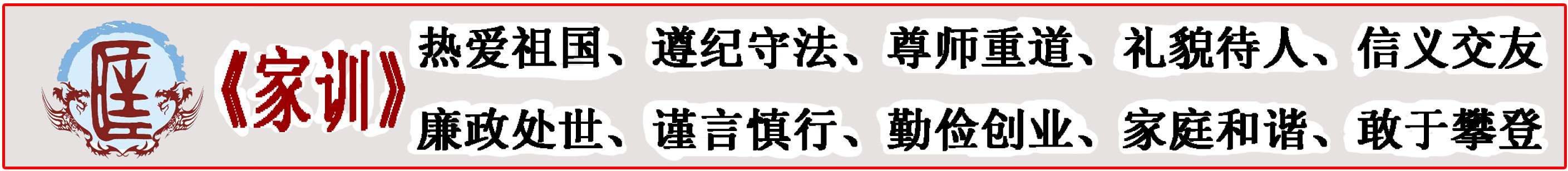
匡亚明(1903~1986年)名淑贞,乳名慈,国辉,修水渣津人。湖北省楚材女子中学毕业,后就读于江西省立乡村师范。曾任修水县第六区妇女主任,1932年2月当选修水县苏维埃第二届妇女联合会主任。经常女扮男装到边远山区做妇女工作。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后,在进化小学任教员。1935年被捕,后经保释出狱。1938年前夫病故,别下刚满月的女儿谷梅,只身潜往泰和县继续从事妇女运动,后转迁北京,与刘作如(交通部高级工程师)结合。五十年代初用自己的全部积蓄组织里弄居民办街道工厂,1955年改名为北京东风电视机厂。“文革”期间被打成叛徒。1971年曾回修水居住一年多,1979年平反,1986年在北京病逝。留有部分诗作。
文章原题目《朱门闺阁叛逆女》
话说上世纪二十年代修水仁乡渣津有个朱门闺秀叫匡亚明(1903~1985),生得苗条硕长、眉清日秀。这样一个亭亭玉立、文弱多姿的千金,却生性倔强。举止泼辣,敢唾弃世俗,能忤逆反上,走出闺阁,参加革命,入党后,曾任县妇联主任,在她传奇式的人生道路上,让青春焕发出绚丽的光华。
脱缰野马
春风飘拂,阳光普照,渣津匡家大屋背的树丛换上了嫩绿的新装。这天,那紧闭的朱门忽然开启,一老妇人蹒珊而出,手搭凉蓬高喊:“亚明,亚明”只有山野的回声,老妇嘀咕着:“就是脱缰的野马!”当她转身向内屋时,突然一双手从背后把她拦腰箍住;接着,是一串熟悉的清脆笑声,老妇自知是淘气的孙女,回转头,只见这女娃满头大汗,挺起已脱下春装、有棱有角的胸脯站在面前。心里想:姑娘大了,再不包脚更待何时?她长叹一声:“咳!是我把你惯坏了,野马不归栓,又干什么去来?”亚明一偏头:“踢毽子呗!“你看你,那像个千金小姐?”“千金小姐又怎么样?”“守闺门,包脚!”“就不”,孙女扭着腰撒娇:“又是包脚,不包,我一世不包。”“你犟得了?”“你又来霸蛮。”
说到此,笔者要回头交代几句:匡亚明白幼父母双亡,这根独苗跟着祖母胡氏和五叔匡紫兰过活,都对其教爱甚严,一越雷池即遭训斥,然而这亚明,生成的天不怕地不怕,你就是给她锁上门,她也有办法扒出去。老祖母心疼孙女,只好且收且放,而对包脚,却不松口,无奈每次包脚,孙女都会嚎啕挣扎,老人力气不佳,自然无法缠住。
一日,老人叫来五儿,两人一个提脚,一个抓手,按在踏凳上拿起根早巳备好的布带,霸蛮给亚明包起脚来。那亚明搓脚打手,叫爹叫娘,痛得要去寻死,这比较开明的五叔本来对缠脚有看法,只是母命难违,只见侄女如此犟性,心一软,手一松,长长布带洒落一地,两人累得满头大汗,无可奈何出门而去。老人有气,“澎”的一声把房门关上。亚明揉着脚打定主意,想开门逃走,谁知门已反锁,她转身扳开本巳陈腐的窗棂钻了出去,一迳跑到离家四十余里的台庄外婆家去了,吓得老祖母心惊胆战,吃不下饭,睡不养觉,好不容易是五叔找到,好言相劝,才回家。
老祖母硬的那一套不行,思来想去变换了手法。这天上午,她发现孙女不在家,想她巳长成了大姑娘,却不守闺训,不读《女儿经》,要坐“洋”学堂,而最让她头痛的是那一双任其放任成长的两片脚丫,再不包,确有辱匡门家风。想到此,她将亚明唤回,等她梳洗巳毕,走进闺门,一脸愁容拉着孙女的手叹口气:“唉!崽啊!你爹娘过世得早,我也无能为力教爱你,眼看老身越来越差,快入土了,只是一事放心不下……”说罢,泪水涌泉。
亚明是婆婆一手拉扯大的,情深意笃,今日一见她如此悲戚,不禁一阵心酸,忙掏出手帕绐老人擦泪:“婆!有什么亭放心不下,你只管说好了。”“唉!说了也没用”,老人顿了顿,望着亚明那刚出搭的大脚,摇摇头:“自古女人缠脚……”心直口快的孙女,见老人转弯抹角还是离不开包脚,不待她说完,紧接:“你又是要我包脚?我早说了不——包——脚!”老人无奈,似乞求地:“你就依我这一回吧!”说着,从怀里取出两卷皮带,把孙女一只脚搁在身上,边缠边唠叨:“乖乖,我是为你好,忍耐一时痛,可免百年之忧,男人就嫌大脚,即是个千金小姐也没人要。”“我不嫁人,自谋生活。”“孩子话,那有女人打单身的?”亚明怜惜老祖母那副菩萨心肠,事已至此,只好就范。
包好脚,亚明痛得不能迈步,她扒在门边哭着,把门捶得“嘭嘭”响:“婆呀莫造孽啊,可怜可怜我吧!”
这边孙女哭,那头老人泪,老祖母是过来人,自然知道这滋味,但只要熬过几天也就好了。谁知亚明把门一关,又几下把带子拆了。
另天,老祖母又来包脚,发现脚带松垮的,自知是孙女做了手脚,这回,她拿来针线,细细地缝了起来。老人前脚出门,孙女就拿剪子剪开。就这样剪了缝,缝了剪。老祖母硬是无法包住亚明的大脚丫,他摇摇头:“就有这样犟,在家从父母,出嫁从丈夫,留给她将来的丈夫去爱吧!”
山乡雏鹰
匡亚明挣脱了包脚的厄运,并不满足。又朝思慕想要跳出这金迷纸醉的朱门。真是心想事成,机会终于来到。
一天早上,亚明被唧唧喳喳的喜鹊闹醒,她起床用过早餐坐着看书,忽见台庄表妹领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来串门。这人叫樊策安,表妹的对象,就读于九江第六师范的学生。落座后接过香茗,樊策安谈起外面打倒列强、除军阀那风起云涌的世界,还说有人来到台庄做报告、讲形势、讲新思想、新思潮,说得匡亚明眉飞色舞,怦然心动,揪着两人硬要答应她去听报告。可是如何让老祖母答应离家出走呢?大家如此这般想出了办法。
说话间,老祖母走进门,表妹大声说:“表姐,我台庄书堂来了个有名的女老师,有水平、有耐性,台庄是你外婆家,何不去那里读书?”
话一提出,亚明当即拖住要祖母松口,加上两人敲边鼓,老祖母虽不放心,但难碍客人面,只好应允。
台庄是离渣津四十余里地的偏僻山乡,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平修铜根据地的中心区域,山高林密,十分幽静。匡亚明来到这里,慈祥的外婆对外孙女自然是百依百顺,娇溺有加,她在书堂平时安心读书,闲时观赏山野景色,间或有山外传来的新信息,自然心旷神怡,分外惬意。
一个秋夜,山雨淅沥,寒气逼人,匡亚明正待解衣就寝,忽然汪汪狗吠,脚步声自远而近,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开了她的门,那就是樊策安和表妹,表妹贴近亚明的耳朵:“南昌的丁健亚摸黑赶来了,快去书堂听报告。”
匡亚明听说是喊她听报告,一股暖流涌上心头,忙带上小册子穿起鞋、擎把雨伞,消失在夜雨之中。
丁健亚是修水早期在省城南昌接受马列主义的青年学生,而当时的台庄山里是传播新思潮的天然场所,丁健亚进山的消息,也早通知了樊策安,鉴于匡亚明的出身,樊策安自是不好贸然答应。丁健亚—到台庄,听了介绍,当即表示同意。
三人踏着泥泞山路来到书堂,只见里面人头攒动、热气腾腾。有本地人,也有外地人。匡亚明未及细看,找个位子坐下,掏出小册子唰唰地作记录:“工农群众要解放,封建枷锁要砸碎”一句句“火爆”话语像春雷激荡着这位少女的心髓,她似乎吸到了新鲜空气,看到了灿烂前程。
报告结束时,鸡叫头遍了,匡亚明大大方方地走向丁健亚:“你讲得太好了!”丁健亚指着她:“你就是那个逃避包脚的匡小姐?好,好!欢迎你做前人没有做过的惊天动地事业。”说罢,几个热血青年余兴未尽,与丁健亚一起促膝而谈,直到风停雨住,月落星稀,迎来了黎明的曙光。
耍泼新娘
这年腊月,匡亚明拜别外婆和村里同学回渣津老家度寒假。
不数日,只见司前几个不常来的亲戚忽然进进出出,热呼起来。一来就同祖母、五叔到侧屋客厅哝哝唧唧,交头接耳,匡亚明心里明白,他们背后的勾当,肯定与自己有关,莫不是……她心理兀自有种不祥之兆。
这一天,客人走了,老祖母笑吟吟地走来:“亚明,恭喜你了!”亚明一听,顿时汗毛直竖,心理忐忑地蹦,预感一场婚姻悲剧即将临头,她红着脸颊,明知故问:“什么喜事?”“唉!许久你不在屋,我们给你找了个好人家。”“好人家,叫什么?做什么?人怎么样?”“是司前一殷实大户”,匡亚明不耐烦:“我是问那个男人?”“嘿!那后生长得细皮嫩肉,一表非凡。”“他为什么不来我家相亲?’”“在武汉,坐洋学堂,约定了明日回来结婚。”“结婚?那我要先看看,谈谈,怎么不相识就结婚?”
谈论间,五叔一脚走进闺房:“亚明啊!你是读书人,难道不知道自古以来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怎能让女儿家抛头露面去谈?”“五叔,不要翻老通书,如今民国年代,讲反帝、反封建,还兴包办?”
这个读书人近来也听到一些风声,他不信,婚姻也由女儿作主,但碍于侄女犟性,便坐下来劝道:“亚明啊!你七八岁我们把你带大,那桩事不依你?看,说不包脚就不包脚,说去外婆家读书也不拦阻你,难道你祖母、你五叔连这婚姻大事都不能作主?”“五叔,那男人我一次都没见过。”“唉!你不相信五叔,难道还信不过年迈的老祖母?告诉你,那后生很有学问,包你满意。”
话虽如此,可亚明却满腹狐疑:“为什么硬不让她和男人见面?为什么来得这么快?”那一夜她想来想去,决定逃婚。
那夜,她和衣而睡,半夜时分,她起来听听,外面无动静,忙收拾细软,走到门边抽开闩,谁知门被反锁。反转身来到窗户边,拉开门帘,这时她才发现,上次被她扳断的窗棂,已换成了雕花石窗,这一折腾,不觉迎来了另天黎明。
太阳照上树梢,厅堂宾客满座,远处唢呐乌拉、锣鼓鞭炮齐鸣,花轿很快来到门口,而闺阁里的新人不吃喝梳洗、不穿戴打扮,一味嚎啕痛哭,跺足踢门,左邻右舍来帮忙的女客,好不容易往她头上插的花被拉下来撕碎,穿上的红衣,也脱下来踩脏。面临起轿,却无一人能劝住这闺女耍泼。事已至此,五叔一努嘴,众人上前七手八脚行蛮,抬的抬,搡的搡,拥出房门,省掉许多礼节,一直塞进花轿落锁。人们深知这女娃脾气,不敢怠慢,抬起花轿就跑。
渣津至司前只有五六里路,花轿很快抬到王家大屋,打开轿门,喜娘和送嫁女把哭哑了嗓音的新娘拥进大厅。早有疑团的亚明,把那被泪水浸湿的羞巾拉开一看,怒声喝问:“新郎呢?为什么不出来拜堂?”
事至此刻,那女宾才怯生生地附在新娘耳边:“他病得很厉害,不能起来,你就……”新娘不待对方说完,一跳老高:“一色骗子,骗我来冲喜!”说完,“嗤!”把手中羞巾撕碎,踏上一只脚,跑出大门悻悻而去。
新人的吵闹,锣鼓的喧嚣,房中的新郎,两眼翻白,一命呜呼。
潜行武昌
再说匡亚明白那日从王家出走,她没有回匡家,走几十里山路,来到台庄,一头扎进外婆怀里,痛哭一场,就此看书学习,接收了不少新思想,一住就是三年。
这期间,匡家老祖母悔恨心情自不必说,几次派儿子进山送钱送物,登门认错,可那犟孙女就是不回。
1926年9月,已是共产党员的樊策安来到台庄传喜讯:北伐军第6军攻克了修城,由共产党人主持的修水县政府宣告成立,并派匡亚明到武昌学习。惊喜中的匡亚明却有心事涌上心头:如不回渣津老家,不仅盘缠一切费用无法筹措,而祖母、五叔纵有不是,也抚育了自己成人,今日出远门不去打个招呼,依情依理不合。可是他们会同意吗?她略一思,有了,就如此这般吧,主意已定,当日上路,赶回了渣津。
终日倚门而坐的老祖母一见亚明回来,喜出望外,转来转去,摸摸头发,看看扮相,乖啊崽呀喜泪双流:“我这调皮心肝长得更标致了。”立马杀鸡剁肉,忙个不亦乐乎。
匡亚明帮着老人张罗,亲切地挨到她身边,嗲声嗲气地:“婆呀!孙女儿想你啊!”“想我又不回来。”“气没消呗!”“死丫头!”老人伸出油腻的手指头一指:“对婆婆也有气?”亚明有意岔开话题:“婆呀,我昨夜做了个好梦,赶着回来告诉你。”老人一惊:“什么好梦?”亚明见祖母停下手中的活,急切地想听梦,卖着关子噗嗤一笑:“哎!莫急罗!”老人擎起巴掌扇了扇:“鬼东西,还是那样刁,讨打!”亚明佯装害怕,退两步:“我说,我说,我梦见姑家盖了新房。”老人一听拉长了老脸,摇摇头:“咳!”诸位,你道为何?
原来老人最疼爱幼女,最相信“周公解梦”,不禁梦牵离情,愁锁眉梢,孙女故作惊恐:“婆,怎么啦?”“咳!你不知道,梦盖房,主不吉,许久无音讯,只不知你姑为何?”正中下怀的匡亚明忙接话:“是不是要我去看看?”老人双眼一亮:“你能去当然好,只是路远迢迢,我放心不下。”此去县城不过六七十里,一路有同学照看,放心吧!”“那就好!”
当晚,老人忙着给孙女制办礼物打点行装,一宿无话;另天黎明,亚明梳洗完毕,拜别祖母、五叔上路。
在奔去武汉途中,姑娘好似脱牢笼之鸟,想着即将来到革命中心武汉,不禁心潮起伏,吟起诗来:
青春念二出闺门,脱却红装去远征。
壮志凌云身不顾,从此誓不返豪门。